
【沂蒙乡愁】第13期
◎陶凯
我极怕冷,过了寒露,几场绵密的雨掠过,几缕不经意的风走去,还没有供暖的屋子很有些清冷,军大衣就成了“标配”:工作时在里面把自己缩成个茧子,歪在沙发上看书干脆裹着它蜷成母腹时代的样子。因为一场预报中的寒流,对这次十一前就获邀约的沂蒙之行,看着手机“天气通”犹豫了几下才成行,扛着一大箱棉衣。
意想不到的是沂蒙的阳光,在清晨的微寒中就昂扬着抬头,及至中午前后,周身的温暖可以用“小阳春”来形容,光影折射下色块堆积的沂蒙,“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便不只是诗人的吟诵,而是大地的图景。溯流而上,我们去沂河的上源,扑进沂蒙大地。远远看去,那一座座被命名为崮的小山岗像平缓大地上长出的一朵朵没戴帽子的菌子,卓然独立。安插在崮原之上的一处处果园,远看着像开成一大朵红花的是苹果,调着橘红暖调的是柿子,空气中流溢着暖洋洋的蜜意。近处的行道树在秋风的撩拨下,变颜变色,作出深沉的姿态。倒是田间阡陌中整齐的油绿葱郁着惹人眼目,朋友说,那就是著名的山东生姜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生姜生长的样子,眼前有两三尺高的青苗肩并着肩,可以相见的根连着根,地上地下都好不壮观。小心思也活动起来:山东真是个好地方,切几片沂蒙山的生姜,投上几颗泰安的大枣,煮上一壶即墨的老酒,丢几块冰糖溅出凝脂的水花,怕不只是能驱赶体内的寒,还能在心头栽上暖吧?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心里哼唱着,车子下了公路,拐进一片村子,一排排两层楼的新村屋舍涂刷着白生生的外立面,也像生姜苗一样,齐整整的。停车场边上是一条山里流下来的小溪,浅浅地唱着,是《沂蒙山小调》的叮咚。几位靠在墙角抽着旱烟袋的老汉,肤色是罗中立画中的“父亲”,露出豁着几颗缺牙的嘴憨笑着给我们指点路径——这里是沂南县马牧池村,新村就是刚看到的两层小楼区,兴建于十多年前,老村修葺后成为全中国唯一以普通群众特别是普通劳动妇女为主题的革命纪念馆,沂蒙红嫂纪念馆。
讲解员小女孩长着一张清秀的脸,是马牧池村年轻的一代,她引领我们走在石块垒砌的村街上,左拐右转到一户石块垒砌的房前,看马牧池村和沂蒙大地历史的女性。纪念馆中心区是在明德英家的旧房子里改建的,她是公认的沂蒙红嫂最早的生活原型。
像是村里其他的房舍一样,明德英的旧居在兴建红嫂纪念馆时也有比较大的整修,只有那些老碾子老磨和水井,记忆着过往。院子里的空地上,仿建了一座过去沂蒙山地区贫苦人家惯常居住的团瓢。“团瓢”,我从年轻讲解员的口里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院子里仿建的那个,据说比明德英家从前为村里看坟时居住的还要好很多,可那也是低矮的门,露天的棚,灰暗的光,我身量略高些,挤了两挤,很难进去。抗日战争时期,明德英先后救援了两位被日本鬼子追捕的八路军小战士,在那四处露天的团瓢里用自己的奶水给奄奄一息的生命输入了营养——用自己乳汁救伤员的沂蒙山红嫂,明德英们,在凄寒困苦中心里揣着光明呀!
我站在那儿,眼睛被牵引着望向团瓢内每一个在灰暗中争相沐浴屋顶罅隙间流转的丝丝缕缕阳光的角落,嘴巴里突然泛起一种记忆中熟悉的味道,淡淡的,甜甜的,带着一丝丝腥味——那是妈妈乳汁的味道!
我知道,我知道!妈妈的乳汁是什么味道,那从生命呱呱坠地起就意味着温情与馨暖的味道。
我是个晚生子,妈妈39岁才生下我,从小体弱多病,父母便舍不得给我断母乳。3岁那年,一支竹筷在外力推动下刺裂了我的上颚到达鼻腔,那之后的昏迷和治疗我不记得,记住的只有剧痛,以及一碗一碗的血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吃饭,只能吃妈妈的乳汁,便比别的孩子有更深刻的记忆:妈妈的乳汁,是淡淡的甜又约略有点腥的味道,并不觉得多好吃,于我,最初是生存的本能,后来是深深的依恋。妈妈的乳汁并不多,随着我越来越长大,捧着妈妈的乳房“开饭”时,连小小的我都能感觉到它越来越干瘪,我又着急又饥饿磨着牙使劲吸吮的时候,妈妈的身体有时会一抖一抖的。
等到我也当妈妈了,在那熟悉的味道中,我常怀抱着粉嫩一团的宝宝,出神地盯着衰老的妈妈看。我是正月里生的女儿,妈妈在年前的冬月摔伤了一只手臂,吊着石膏做各种好吃的给我补养,叨念着说:“妈妈的奶水是血变的啊,得加强营养呢。”劳作中的妈妈手臂枯瘦干瘪,苍白的有些透明,能看到浅青的血管,血管也常常是枯瘪的。我就想,妈妈的血是不是已经抽干了?妈妈的血是不是都化成乳汁变成营养到了我的身上?我的心头泛起三五岁时依恋的母乳的味道,原来,那不只是我嘴里迟迟未愈的伤口在渗血,也饱蘸着妈妈的精血呢。
站在明德英家院子里的团瓢前,母乳那甜腥的味道让我的身体不自觉地战栗,似乎在那一刻,我才真切感受到,我的脚下是沂蒙大地啊。
几个白天又黑夜,我沉浸于沂水蒙山间,去触摸年少时就知道的红嫂,去触摸深情又伟岸的母亲们,在历史资料上,在亲人讲述里,在后代赓续中。
天下的妈妈都一样吧,为了孩子,为了心中的深情,她们最能舍弃的就是自己,她们付出全部的也是自己。我妈妈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军老兵,为了抢救伤员多次输血,从我有记忆起,她的身体就非常弱,现在想到我比更多的孩子多吃了许多年自己母亲精血熬成的奶水,心里有不忍,也有更多的眷恋。母亲虽然不到半岁就成了父母双亡的孤儿,幸得赖有情有义的亲人们,寄人篱下也好好长大,她的爷爷还卖房子卖地自己去当长工供她读到了高小毕业,比当时很多女孩儿,多了一扇看世界的心窗。投身那支叫“解放军”的队伍参加革命,是母亲自觉自愿的自主选择,因为她听到看到了解到感知到那支队伍是向着光明与美好的,能带她到一个全新的天地全新的世界开创全新的美好生活。沂蒙的红嫂大多不识字,在她们那个年代,叫“睁眼瞎”。但我相信她们的心里是亮堂的,她们一定是看到了希望,感到了温暖,得到了启迪,然后才会拿出行动甚至是豁出命来去支持能给她们带来美好未来的那个主义那个政党那支队伍!她们是赤贫的一群,在向着光明与温暖前行的路上,以各自仅有的一切回报带她们前行的力量:面对生命垂危的伤员,母亲一次次挽起袖子献出鲜血,沂蒙的红嫂们则用自己精血凝成的乳汁与死神拼争。她们都没有喊什么口号讲什么大道理,却都拿出了自己所能拿出的全部。
马牧池村一个院落里有一块跟中国地图很像的石头,上面刻着歌词:“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这就是沂蒙的红嫂们包括我的母亲当年的选择坚持的力量。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整个沂蒙山区七八十年来涌现出了几百位红嫂 ,有跳进冰河中用身体做桥墩搭浮桥的,有送儿子或者丈夫上前线的,有掩护抚养革命下一代的,有走在新时期物资拥军智力拥军科技拥军教育拥军前列的,有人是老红嫂的女儿儿媳孙女们,也有的是军属军嫂军队和军人的朋友。那天,去看新时期的新红嫂朱呈镕,不巧她前几天刚扭伤了脚,为了给一批刚刚复员的年轻人做报告,六十多岁也是老人的她穿上鲜红的衣裳,精神饱满地来了。我拉着手扶她上楼下楼,那手真是粗糙,像当年整日调剂药水的母亲。
我的妈妈比明德英妈妈小18岁,那是一代人的距离。我的妈妈为新中国的建立浴血奋斗过,也享受了新中国瑰丽的阳光,还留下了青春勃发的影像。明德英妈妈能拍照片的时候,已在人生的暮年,脸上满是岁月印痕的沟沟褶褶,她的年轻和美丽已不再。我在很多地方可能都看到过她的照片,可还是没有记住她的脸,她那张典型山东人的窄额头宽颧骨面相,我在很多山东妈妈的脸上看到过,我自己家山东籍的老嫂子也越来越长成那样的面庞,不大的眼睛里有坚韧,平和的脸庞上有倔强。山东大地有很多这样的妈妈,就像沂蒙大地上明德英是红嫂的代名词,但红嫂绝不是一个明德英。
晚上,风萧萧涌起,拍打着窗户,我把两床被子垒成一个暖暖的小窝儿,蜷缩在里面做了一个梦:好多老妈妈抱着我,她们的乳房鼓鼓的,我的脸贴在上面,嗅着甜腥的香,抬眼看去,她们的脸是明德英妈妈的,是老嫂子的,最后幻化成母亲最美时的样子。我咂巴着嘴,每一颗味蕾上都欢跳着妈妈乳汁的味道,那是淡淡的甜,加上血脉的滋味。
那么多、那么多沂蒙的红嫂站在那边,有的有名字,有的没名字,有的是照片,有的是画像,高低错落,是油画家可以画成母亲群像的肤色,将一道道晨光洒下。有只暖暖的手抚在我肩头:来,跟妈妈喝奶了……

作者简介:陶凯,女,满族,中国记者协会、中国铁路记者协会会员,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资深记者、编辑。新闻作品曾多次获国家、省、市级新闻奖。创作作品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编辑作品入选国家图书奖。作品散见《青年文学》、《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报》、《中国纪检监察报》、新华网、人民网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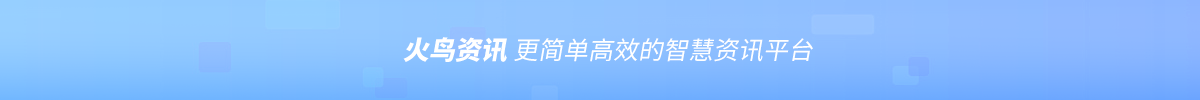













精彩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请遵守评论服务协议
共0条评论